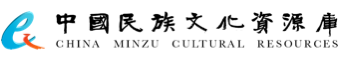
克鲁伯,历史特殊论学派代表人物,生于纽约的德裔犹太人家庭,是博厄斯最年长、著作最多的学生,博厄斯的第一个人类学博士。曾任美国人类学会主席,获得过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代表作:《人类学》、《文化的特质》、《类型与文明》、《北美文化区和自然区》、《加州印第安人手册》。
克鲁伯认为文化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学习获得的,即是“超有机体”,不受较低层有机体影响,如遗传因素等。文化有其特点和自身发展规律,文化人类学者只需研究文化自身。他的论文《十八条宣言》概括了其历史特殊论观点。一是不研究文化的因果关系,不研究人、心理、生理、地理环境要素,只研究文化自身及其关系,即文化事实和人的创造物;二是文化不存在普遍法则,没有进化阶段,没有统一的心理活动,没有任何决定论的东西,最多只是趋势。他后来专门撰写《超有机体》的文章,再次坚持文化是独立于人,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和规律,并强烈反对斯宾塞等人将文化比喻成有机体,即社会有机论的观点。
克鲁伯的《妇女时装300年》研究妇女服饰变化,目的是向世人证明,作为文化的一种要素的服饰,其发展有自身的规律与轨迹并不受人为因素的影响,这也是对超有机体的证明。他又于1944年出版《文化成长的形貌》,试图找出哲学、音乐等文化的成长周期曲线。
在克鲁伯看来,文化系统可分为两部分:基本形貌和次级形貌。基本形貌指与生存、生计相关的文化事务;次级形貌指与创造力、艺术活动有关的文化活动。它们的区别有三点:(1)基本形貌面对现实,次级形貌面对价值。因此,基础形貌的动力是实际利益,次级形貌的动力是创造力。(2)基本形貌建立在显示的客观条件上,受其制约,并反映人们的利益和面对的自然环境。生计模式对于次级形貌的发展是必须的,但是次级形貌又有其内在的本质和规律,在特定的情况下是独立发展的。(3)基本形貌的历史是积累的,而次级形貌由于创造力的多变,所以不是积累的,往往会中断或演变为其他的东西。构成次级形貌的各文化要素都有其历史发展模式,每个文化要素都要经历成长、发展、巅峰和衰落这些阶段,记载和绘制这一发展模式就是成长曲线(这一曲线并不受人的影响)。
1934,克鲁伯出版《北美的文化区与自然区》,系统提出有关文化区的看法:(1)首先,文化区虽与自然环境有关系,但前者不受后者决定,最终是由于由文化本身的作用;(2)其次,文化区都有文化高峰,指文化特征最丰富的地方。在此基础上提出“强度”这个概念,指文化达到并维持文化水平的程度,强度较大的文化是那些文化特征清楚、制度和关系明确的文化。一种文化的高峰是该文化区内的中心,这个中心向四周释放影响,一直到该区的边远,而强度也逐渐减弱;(3)最后,划分文化区最难之处在于边界的确定,两个文化区相邻地域的文化总是含混不清的。也就是说交界处的两个民族拥有的共同文化要素要远多于文化中心地。
此外,他在考古、语言、历史学等多个方面都有研究。他反对摩尔根,也反对里弗斯亲属称谓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将亲属称谓分为八个类别,将亲属称谓和亲属制度联系起来。
参考资料:
[1]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流派:文化研究的历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2]宋蜀华,白振声.民族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04.